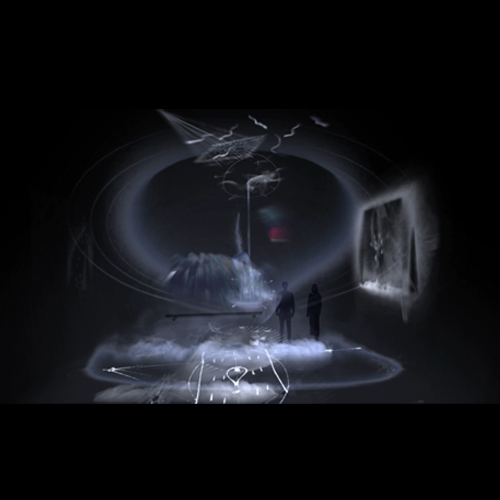主体的终结:VR艺术的游戏性体验
Termination of Subject:The Playful Experience of VR Art
2017-07-11
作者:李怀骥
创作时间:2010年4月
主体的终结:VR艺术的游戏性体验
【摘要】:“虚拟现实”作为数字技术中最神奇的科技成就之一,正在把人与机器的关系推向极致,然而这种极致所导致的悖论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张力,深刻挑战了我们作为人而存在的知性范畴和感知的界限,并最终改变我们对技术与自身的看法:基于人机共生意义上的日甚一日的技术变革已不仅是我们生活中恒常的特色,未来的发展抑或是二者在非隐喻意义上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过程……
“Virtual Reality” as one of the most miraculous scientific payoffs in digital technique field, is pu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to an acme, and the antinomy this acme caused, together with the complex tensility between the two actors, has profoundly challenged the intellectual borders of human being, it will eventually change our point of views towards techniques and ourselves: the technical revolution based on man-machine symbiosis doesn’t only represent a constant character in our life, a future development or a non-metaphorical competition process between them…
转变创造与交流方式的技术:“虚拟现实”作为艺术语言
在以往的艺术实践中,艺术家总是或多或少受到物理世界固有逻辑系统的支配,难免为空间、体量、时间性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所束缚,而“VR技术”作为数字技术中最神奇的科技成就之一,为艺术家提供了赢得这一自由的手段。它打破了以往艺术实践的经验模式,在它创建的世界里,任何一种信息以及任何构成其原始存在的物质性因素,都可以变为可以控制的电子“变量值”,因而当我们置身于其间,一切体验总是特别的,所有事物都变得更加本质化,而且倾向于个人化。正如我们所知,VR世界所预设的感知框架是基于软件程序不断地再生产、复制与发送一体化的过程,因此该世界所蕴含的阐释前提,已不再是常规语境下倾向单向度交流的元叙述,而是存在于“一种新的联想链接和无穷尽地重新建构与重新界定的交互、转换与涌现之中”。
这一无限扩展的人机界面不断超越我们经验感知的界限,进而能够帮助我们以数字编码的方式去再造另外的感知世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者莫里(Murray)从认识论的视野考察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前景,并就其对未来艺术的可能性影响展开了深刻论述:“我们抑以将它作为一种创制可能世界的本体论机器来加以理解……虚拟现实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可以访问的空间、亲历仿真之境的体验,而且把我们带到可以将现实中的智慧和梦想付诸实施的地方。”
从亲历仿真之境到完全沉浸性的呈现空间,由于艺术家大多倾向于对科技工具及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与干预意识,并且不断在寻求与社会建立平衡的努力,因而总是处身于最先对当下的科技进展作出反应并积极施加影响之列,正如保罗(Paulo)所指出的:艺术的发展总是同等地反映由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变革。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媒介加以运用的艺术形式,我们称之为“虚拟现实艺术”,简称“VR艺术”。
VR艺术依托于当今科技前沿的数字化空间,这一空间的特殊优势赋予了艺术创造、呈现以极大自由。它诉诸于仿真和艺术实践的虚拟化,可以“通过无所不在的计算”来决定创造物的形式和行为,因而对于当代艺术而言,此等意义上作品的参与、发布等形式,能够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既有的艺术机制及主流话语权力之外,并与之形成对等性存在(它不仅超越了地理和空间障碍,而且享有现实世界所不具备的整合平台的功能,具有实时互动和全球化等特征)。这一意义为扩展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认识论视野开启了一个额外的维度,其中流动着创造语言叙事的极端自觉和先天的独立性,因此它不仅是一种倾向或风格,而是正在形成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并最终发展为新的美学领域,尽管目前仍以低姿态的实验性面目出现,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是从艺术变革、精神实验力量的自我超越这一角度,已经成为艺术现代性进程中最具时效性的活力点。它通常会参与到网络世界中,将艺术的生命力植根于当今世界文化的共时状态中,构成了当代文化影响社会视听的更为广泛的反馈面,而网络多重身份存在以及非中心化特征产生的独特言说方式,为艺术家带来了全新的创造体验,甚至促动着艺术家整个创作意识的转化,同时,这种建构于网络界面的极具现在进行时特征的语言形式和随之产生的新的艺术观念,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形成潮流,并且正在以越来越成熟的面目进入艺术史的视野。
艺术作为“过程”
作为现代科技前沿的综合体现,VR艺术是通过人机界面对复杂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与交互的一种新的艺术语言形式,它吸引艺术家的重要之处,在于艺术思维与科技工具的密切交融和二者深层渗透所产生的全新的认知体验。与传统视窗操作下的新媒体艺术相比,交互性和扩展的人机对话,是VR艺术呈现其独特优势的关键所在。从基本概念上说,VR艺术是以新型人机对话为基础的交互性的艺术形式,其最大优势在于建构作品与参与者的对话,通过对话揭示意义生成的过程。德国艺术家杰弗里·肖(Jeffrey Shaw)在其装置作品《知觉之门》中,构造了一个由信息空间、可视化系统形成的宗教场域,该装置使用荒谬式、超现实式的语汇,以现实世界不可能出现的写实性,引领观众进入了一个无法抗拒的宗教世界,观众在观察作品时,无意识地被引导进行宗教仪式似的动作。艺术史家爱德华·山肯(Sanken Edward)对该作品进行了这样的评论:“当观众面对着由软件和计算机界面形成的神像祷告时,这一切充满了讽刺性和荒谬性,这种隐喻性的虚拟物,通过预先设置好的程序让观众服从于科技力量,同时更严肃地思索人类魔力的衍生物——宗教。”
从技术应用的整体视野来看,VR艺术作为真正在现代科技领地付诸行动的艺术,赋予了艺术行为一种新型的技术美学色彩,在众多VR技术中,由法国爱迪斯通公司研制的虚拟现实软件Virtools以人性化的界面和超强的整合功能,为艺术家创作VR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新的可能性。该技术包括丰富的行为模块、人工智能模块、直觉式界面和多个行为模式,这些特殊模式可以帮助艺术家在虚拟世界中实现对周围环境的信息反馈,具有强大的虚拟现实沉浸效应和体验功能,交互方式也更接近于人们的自然行为。
艺术家通过该技术,可以采用更为自然的人机交互手段控制作品的形式,塑造出更具沉浸感的艺术环境和现实情况下不能实现的梦想,并赋予创造的过程以新的含义。如具有VR性质的交互装置系统可以设置观众穿越多重感官的交互通道以及穿越装置的过程,艺术家可以借助软件和硬件的顺畅配合来促进参与者与作品之间的沟通与反馈,创造良好的参与性和可操控性;通过视频界面进行动作捕捉,储存访问者的行为片段,以保持参与者的意识增强性为基础,同步放映增强效果和重新塑造、处理过的影像;通过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形式,将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结合在一起,观众可以通过自身动作控制投影的文本,如数据手套可以提供力的反馈,可移动的场景、360度旋转的球体空间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沉浸感,而且可以使观众进入作品的内部,甚至操纵它、观察它的过程以及参与再创造的过程。
VR艺术整个创作、被接受的过程,自始至终表现为艺术家与参与者之间交流与回应的扩展性活动,其生产过程因而是艺术创想、技术制作和观众参与再创造的一体化过程,很显然,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多元组合的综合性工程,该过程打破了传统的一元化行动思维。由于参与者的回应是直接的、现场的,因而作品生成于一种多向度思维,即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反复变幻着思维方式,并且总处在“活动”之中,同时这种活动须在接受者、参与者的干预、指令下展现,而非任何一方独自完成的活动。此类作品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并非最终追求,重要的是其形式引发的过程本身。博思玛(Brolsma)在《作为体验的艺术:遭遇活跃的受众》一文阐述了该过程的意义:“艺术家与受众的对话方式由此转向了作为工具与参考系的科学……二者身份正在彼此渗透,受众解放到合作者、参与者的水平,他们受到上述过程的挑战,反过来推动了艺术阐释的进一步发展和艺术思维的多向度交流。”
行动的艺术:参与再创造
随着VR艺术的崛起,传统意义上的观众日益向“参与者”、“交互者”甚至“玩家”转变,艺术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被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浸入式体验。作品可以设置多种发展和变化的可能性存在,如设定实况捕获等形式将观者结合入想象的视频中,为观者参与创造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通过超链接或嵌套式结构设置多文本框架,参与者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对作品施加影响,通过系统提供的技术帮助去完成对作品的再创造;也可以基于自身的动作和行为,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和逼真的感觉输入去影响作品,在开放式的互动场景与完全自由的路线选择中浏览作品或与之交互,从而体验一种能够与自身行为产生回应的浸入式感觉;参与者可以从自身视点或者第一人称视界出发(或通过角色扮演),在其中创造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们的每一次参与,都可能创造一个重新结构了的新文本,这一过程用尼采的话说就是“重新制造自我”,因为作品空间变成了可由观众自主操控的多用户环境下的信息支持系统,该系统将创造物(可编程的实体)变为可以由计算机处理的数据或者可操控的信息。
在此意义上,艺术家的任务其实是构筑一个参与者活动的平台,以一种网络交互或者基于沉浸式交互环境等形式去创造参与性叙事、塑造参与者的特定体验。它不再像传统艺术那样,艺术家能够独自操纵一切,决定一切,而是可以通过参与者的介入、干预和选择的过程而使作品最后完成,于是,沉浸性、流变性、交互性构成了艺术生产和技术装置的核心,此等多感知的特性意味着艺术文本的不确定性或多文本化。这使艺术家越来越重视艺术生产的过程,而非作品被接受的结果,因为VR艺术的优势并非是追求某种价值在纯粹物质性领域中的不朽,而是如何建构作品与参与者之间的动态交流和深层次的互动。
由于VR世界中“数字”决定着创造物的形式和行为,任何可能的物理结构或任何一种信息,都可以变为可以控制的符号系统。该系统不仅能将数据转换成可知的影像来模拟现实,而且具有属于其自身的现实,即另一种现实性和真实性,它扩展了艺术家的认识论视野,并影响和改变着我们对艺术既有的知觉模式,甚至在某些潜在层面上颠覆了以往认知实存下的艺术运作方式和逻辑,因此,VR技术对于当代艺术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对感知经验的探索与重构,而且在于对传统本体的认识论方法的超越。
它首先打破了传统视听界面下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进入VR艺术,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多感交互的新的经验世界,该世界给予参与者的交互界面多呈嵌套式结构,参与者从一点可以进入无数可变的空间,他们同时被赋予了一定的自主权,能够在共享的同步电子空间中去支配自己的作为。这种作为的有效性,需要一种应对如何使参与者的介入、干预和选择所必备的技术支持,以及创作和测试该作品的技术操作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艺术家为促进参与者的再创造建立舞台,并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或以人机共生的形式付诸实施。该特性需要一种可行性的多向度艺术思维来支撑,一般基于人机界面产生的新的认识论方法,通常以强调观念的流动性、形式的游戏性、非中心化为特征。
整体而论,在VR艺术基础部分的构建中,暗含了一种打破传统二元论的潜力,而这种潜力的进一步发展将使艺术家获得一系列新的方法论,并由此形成一种建构于计算机界面的新范畴的美学思想,此时的艺术不再基于过去的决定性美学,而是由拥抱这些独特的数码特性的新的美学经验所塑造,艺术体验是交互性而非被动型的,此时的艺术家,就是为激活艺术生产的可能性法则创造语境的人,他们甚至将创造的权力赋予了参与者,自己承担起推动者的角色,而非创造艺术作品的唯一主宰者。
“游戏”:VR艺术的终极性体验
“游戏是人类心灵生活的戏剧模式……它是亲密而安全的,使我们能够分享自己内心最深层的幻想。”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游戏通常以作为构成人类基础文化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
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游戏”是异质性的生长点,一些研究者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艺术与游戏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游戏触及着人们的深层心理,并且涉及到关乎艺术本源的复杂问题,因为游戏性质的艺术形式更能直接地涉及到艺术的“元问题”。尽管对于它的归属及核心审美体系还存在方方面面的争论和亦褒亦贬的评价,但是互联网非中心化存在以及多重身份实体,构成了艺术信息化转型的新秩序,于是建构于网络界面的具有游戏性质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开始吸引艺术家们的注意力,而游戏性质的VR艺术更是呈现出特殊的激进意义,甚至被认为是“能够生产艺术的艺术”,因为游戏模式下的VR空间所具备的强大的整合功能使之更接近于“元空间”。
由于艺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不同阶段来自技术领域的影响,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为开拓VR艺术的游戏性潜质带来了强大的驱动力,基于艺术家、参与者和智能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游戏性”成为三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和作品赢得受众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VR艺术与生俱来的互动本质决定了其游戏性潜能,其终极体验因而是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实现并呈现其特殊优势的。循着这一思路,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趋向于一种建构于网络界面的游戏性质的艺术探索,这种探索无疑使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最原始最有力的选择,它通常诉诸于网络非中心化存在,在非物质语境中生成,因此具有非物质化的知觉穿透力。
对于具有游戏性质的VR艺术而言,作品所预设的鉴赏者可以被称为访客或玩家,艺术思维因而是一种从艺术家自我出发,在参与者的干预、指令下进行回馈,不断展开、不断活动的思维。与常规艺术不同,该艺术形式可以赋予参与者一定的自主权和可操控性,允许参与者进行多种形式的操作,或者赋予其诸多角色。艺术家可以在作品中构建依照游戏规则行事的操控方式,某些作品甚至能够感知参与者的存在,并针对其运动或行为起反应,它将允许每个参与者从几种预先设置的任务方式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其结果便是形成了艺术家与参与者之间的“交互主体性”。参与者可以通过物理界面对核心冲突进行控制,作品结构也可以基于多种链接,而情节发展基本上取决于交互者所做的选择,范围可以从虚拟导航、链接叙事、三维世界的创造,到组织屏幕上的陈述世界、多用户环境等。
艺术家罗纳德(Ronald)的作品《迷宫》,呈现了一个完全独立于现实空间而存在的游戏般的虚拟现实作品,观众(访问者)可以通过网络界面探索、超越不同级别的游戏空间,而网络文本则转变为结构和“数据化身”,其中的无序元素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可以对游戏事件进行永无止境的重新编写,界面成为储存潜意识的仓库,访问者越深入这个世界,就越能感知它的无限本质。
互动编码技术是VR艺术的本质属性,艺术家可以参考游戏般的结构,运用多种方式设定作品中的游戏参与,而实现这种参与首先需要一种应对和测试该作品所必备的技术操作能力,使技术支撑艺术,艺术与技术交并。对作品界面或运动导航模式的探索,一般经由技术人员编进为它所设计的结构程序中,把作品的叙事发展与通过参与者的干预、指令所发生的多种变化进行编码,并符号地将它付诸行动。它遵守互动游戏的规则,即作品结果的开放性,而过程的开掘与认同,所根据的是构成游戏音像意义的叙事策略和能够支配游戏的可能性法则。由于作品的基础架构基于艺术家、参与者与智能机之间的交互、协同与共生关系,参与者由此进入到与作品的深层互动模式中,从艺术家的实践经验来看,此时的观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玩家,多数情况下他们将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并且被当成是提供新的呈现可能性和经验的方式。
从认识论方法关于展示存在的视角来看,“游戏”体验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性过程的积淀,与VR技术和当代艺术结合,构成了独具创造力的技术性投射系统,该系统体现了艺术家与智能机之间的新型协作关系,其最大特点是以人机交互、人机共生下的艺术思维保持其生命力,因而成为新媒体艺术中最具整合特征的语言形式。它显然不是纯然的游戏,却使观众以游戏的方式获得一种超出以往认知范畴的“发生”过程中的艺术体验,艺术家的潜能由此得到进一步开掘,此时的艺术家,甚至承担起为“网游”创造无限制进化系统的推动者。
这一意义不仅刷新了以往人们对游戏的概念和感受情绪,而且明显构成了对主流话语和统一性话语权力的颠覆,同时也体现出对当代艺术一些本质性问题的突破,这些突破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挑战的方面看,这种建构于网络界面的艺术形式,对当代艺术的一些常规套路、规范化方法以及常规艺术机制、策展体制构成了根本性的突破(包括创作层面上的方法论、价值观等),同时也挑战了国际既有的展览机制和艺术制度的极限;从艺术推动的方面看,它把当代艺术中具有时效性的极端原则推进到了一个极致,呈现出一种最为原始而前卫的知觉表达,游戏模式的VR艺术同化了以往时代所创造的呈现模式的力量,构成了对既有视觉经验系统的对话或者再造。
然而从技术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建构于此类技术环境下的艺术发展也潜伏着一定的危险性,当我们沉湎于科技优势的同时,有时也会不知不觉沦入纯粹技术的陷阱,虽然从较积极的一面看,该艺术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艺术的集权式面目,使得艺术主体不再被客体化、工具化的世界所控制,然而却造成了主体的异在性,甚至存在着自我同一性的虚构,对于创作者而言,还存在着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矛盾、科技工具在认识论和内在感知双重意义上的悖论,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拟世界在创造新语境与意义生产上的表现性甚至“给人展示了世界大识大同的生灵降临的希望”(马歇尔·麦克卢汉),其实我们所面临的是深刻地挑战我们如何定义自身及周边世界的新问题。
面对互联网非时间、非物质化存在的虚拟艺术世界,传统意义上的观众日益成为充满自主力量的参与者,人们对艺术的认识也不再是一个画地为牢的个体意识层面,而是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人机双向建构给艺术带来的令人吃惊的潜力,然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定的悖论性,应该把它视为工具理性的表征加以批判。在英国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一个题为“命令与控制”的展览中,艺术家用高科技手段创作的作品体现了人们对现代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技术与机器所持的困惑的情感,并提出“是人在掌控技术,还是技术在控制人类自身”的疑问。
正如我们所知,艺术作为人类情感与理性的产物,必须超越技术的限制,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德·穆尔(Mul de .J)的洞见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我们期望未来艺术会建基于“虚拟现实”,但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会日渐频繁地用于生产最糟糕的艺术垃圾,从而助长消费主义和我们的“对存在的遗忘”。
面对主体的终结
传统艺术中的能指和所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深陷于观念与语言逻辑的角力关系中,难以继续生成二者作为符号力量的敏锐度,然而这一情况由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而受到巨大冲击,对于当代艺术而言,VR技术的激进意义是为建立相对独立的能指世界提供了技术条件,它对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在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之间找到符号的意义,从而超越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之外建立起超自然的根基。从技术投射的视野来看,这种根基的奠立是由原始的能指向超自然的、智能性的、游戏性的能指系统全面进化的过程,而该过程导致了经验主体的终结,并继而导致一种建构于计算机界面的“新的主体性”的诞生。相应地,对于当代艺术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开始从一种主体性变成一种投射性,因为从艺术实践的层面来说,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可能发生的结构性改变。在VR艺术中,新的能指世界可以反作用于艺术作品中的世界,并最终归结为与这个世界具有对等性的另外一个世界,该世界消除了我们关于二者的本体区分,并促使我们在一种流变性、游戏性的感觉中对二者的知觉进行重新确认。
实际上,所谓主体的“终结”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过渡或者回归,从艺术自主性原则的一面来看,VR艺术由之获得了开端性的基础。在VR艺术中,形而上学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或新的未来,于是艺术家的形而上思维从传统经验认知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且随着主体的“终结”或“回归”获得一种新范畴的“持存性”,同时这种持存也可以作为一种介质转换到另外的系统,并最终化为一种世界图式中的在场状态。
如果说传统概念世界还保留了形而上学生存论含义的历时性结构,并把世界图式看成是形而上学世界概念的终结形态,而“虚拟现实”世界则是隐喻性地提供了一个对形而上学的先验观更为激进的视角。当艺术家进入这一世界,一种虚拟化的知觉模式与传统艺术经验固有的价值系统之间的对话便随之而生,此时的计算机界面就每一个艺术个案而言都是图像语义结构的一个方面,能指与所指作为艺术生成过程中可感知的前定要素或前定的规律性,失去了它们既有的本源地位,因为我们出入任何一个界面,都牵涉到二者通过一种新的陌生关系、超链接甚至无穷尽地重新建构与重新界定去充当其组成部分的所有界面。这种情形打破了以往我们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同一性思维的盲点,艺术思想被遮蔽的一面经由一种非概念的、非话语性的界面所照亮,因为此时艺术生产的过程被置于虚拟世界总的概念框架之下,构成了对艺术既有逻辑系统的破坏和以往所有形而上学元叙事的消解,艺术生产最初也许建立在技术支持系统(如VR界面)自身同一性原则之上,但是随着二者的重新配置,艺术家逐渐趋向于自身的客体化,而此时的形而上思维却获得了最大可能性的完成和聚集。
在此情形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结构被极端的推动,二者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视界所形成的基本概念,而是迫使我们将视觉与知识的体觉模式结合起来,从而构造了一个超越于视觉现实的新的知觉范畴。该范畴之于计算机界面而言体现为图像语义结构的异构化倾向,这种倾向涉及艺术与技术的去中心化,并最终导致了艺术家的“终端身份”,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曾经是主体的艺术家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他们只是作为“终端身份”而发挥作用,因为艺术家的此在归属于生成,从海德格尔的基础性的本体论视野来看,此时艺术家的意义是“作为生成的存在”而存在,艺术“就其本性来源而言,存在让其自身从生成那里得到思考。”(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作品本身仅是艺术家观念和视野的投射,或者是一种过程的隐喻,该过程恰如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的阐述:“艺术家、作品、参与者三者之间形成的回路(艺术生产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每件作品都变成了一种行为主义的塔罗纸牌包,……参与性、协同性作为其基本原则的反馈,提供了可以由观者无穷地重新洗牌的同等物,并且总在不断地生产意义。”
在此意义上,VR艺术继续了一种游戏性或称“后影像”的实践,但实践的重点已从讲究目标转向注重艺术生产、生成的过程和观众参与性再创造的过程,这种过程也提炼出了相应的方法论和新的艺术制度,并且涉及到人机共生在相应范畴中对自身的定位,艺术由此从它的内在领域中走了出来,越来越不受边界限制,越来越多地由链接来维系,这种变化的潜流甚至使我们趋向于从编码的维度去理解一切创造性活动,通过符号界面进行交流,就此形成了一种建构于计算机界面的新范畴的技术诗学——“交互性诗学”。
然而人机共生的双向发展也带来一系列的制度限制,机器无所不在的控制重构了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恰如福柯所言:权力内在于参与者之间而存在,其中由参与者所采用的技术建构而成。尼采也认为,这种过分强调过程的艺术生产活动,更接近于权力意志的本性,因为创造本身并非是理性的自身立法活动,而生成的发生过程却往往是权力意志驱动下的创造活动,也就是说,这种发生过程往往不期然而然地被操作者内化,或者向着操作者的自我转化,从而使新的知识权力从创造性活动中产生出来,成为一个自我控制的新领域。正如我们所知,技术在生成力量的同时也生成了反力量,有时围绕技术而引发的参与性从根本上看是一种知识权力的建构行为,它的纵深之处,制造了相关事物在角色、权力和对象中不断加剧的分离,技术的颠覆性力量由此体现。相应地,VR艺术一方面作为带领我们进入意识本质阶段的载体,另一方面也为权力意志创立新的价值原则提供了技术条件。
洞观知性的回归
人类主体与信息机器之间的“共生关系”抑或“精神联姻”,预示了一种复杂而含混的本质,无论是基于批判性的社会分析,还是乐观主义诠释,都聚焦于技术的可控制性、权力以及自身的异化等问题上。人类制造了像人一样的机器,使得机器获得了人类命运的赋形,而人也获得了机器的赋形。依据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赋形势必对人类自身造成无所不在的控制,进而导致价值和意义的缺省,甚至使之在某些潜在层面陷入不可逆转的境地,在更深的知觉层次上,甚至带来一系列身心问题,因为人几乎变成了自己所创造的生物,以往作为人而存在的“人类的原始形式”正在变得过时,人类主体不再被传统生存世界所控制,而是正在进入一种“后人类的生活模式”,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新的技术科学正在帮助我们重新创造自身,这时,甚至不能把我们划分为人类,“这是一种人已经变成杂种的、可渗透的、混合的与复杂的实体,在其中身体显示为性、物种与机器不确定的、杂种的混合……”(阿斯科特《变化的建构》),格雷(Matthew Cray)也认为:我们正处在哲学与人类生理学的末日,由于哲学本质上基于生理学,这个过程将决定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后人文主义价值观。
从自然世界必然因果秩序的角度看,无论是科学探索,还是艺术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所引发的问题,都是与提供意义参数的内在制约因素一同起作用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有效调控技术介入所产生的后果,毕竟,当我们浸薀于VR世界这个自位一体的感知框架中的时候,无疑将获得更为远见卓识的洞察力,它触及了我们的深层心理,并进一步影响着我们的知觉模式以及内在的精神诉求,甚至影响了我们有关形而上思维的总路线,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观人类知性的未来并扩展其疆界,从而去理解逐渐消失的真实和表层之下不可见事物的重要性。然而,当我们有限的理解力面对无限的虚拟世界时,势必我们的介入是不成熟的,抑或我们对该世界的定义尚待未来,但是,作为一种后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未来人类知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世界并非永远是独立于我们心灵之外的存在,而是至少能够唤起我们的各种原始动力,或者帮助我们重新寻找新的价值尺度,以此引导未来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VR艺术也毕竟不是纯然的游戏或永远的非知觉领域,也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式、一个批评概念或美学概念,而是可以作为社会的异在力量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藉此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探问和文化价值的表达。
迈克尔·海姆(Heim Michael)在其引人注目的《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中阐明了一个重要论点,即最终的虚拟技术是一种哲学体验:“未来世界也许不得不再次发掘一下非常古老的形而上学领域,但所用的开掘工具却是计算机模拟的虚拟实在机——出类拔萃的形而上学机……虚拟实在的本质最终也许不在技术而在艺术,也许是最高层次的艺术,它的最终承诺不是去控制、逃避或娱乐,而是去改变、去赎救我们对实在的知性。”
参考文献
[1] 瓦尔德·本雅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胡不适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2] 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周宪,许均译,商务印书馆,2000
[4] 德·穆尔:《赛博空间中的奥德赛》,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翟振明:《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孔红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黄鸣奋:《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学林出版社,2009
[7] 格雷:《后人类的可能性》,曹建波译,三联书店,2004
[8] 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桦译,商务印书馆,2000
参展作品

部分参展作品